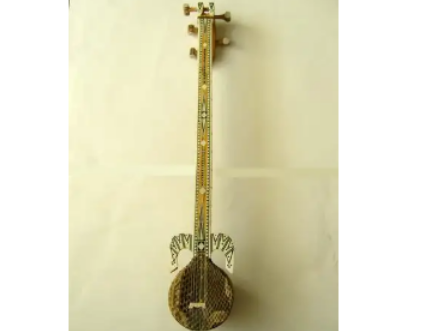1273年2月,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在坚守六年后,终因外援断绝,只得开城向元军投降。元军在占据长江上游后,积极调整部署、调兵遣将,准备与南宋王朝做最后的决战。1274年6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兵分两路南伐宋朝:左路军由博罗欢、董文炳以及降将刘整率领,攻取两淮;右路军由伯颜、降将吕文焕率领,顺江而下。虽然宋军守将张世杰、边居谊等人在鄂州等地顽强抵抗伯颜的大军,但终因寡不敌众,纷纷溃败。元军占领长江中游重要门户鄂州后,“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皆望风降附”,在吕文焕的招降下,黄州、蕲州、安庆等地守将不战而降。

网络配图
此时身在两淮的宋朝降将刘整唯恐吕文焕立下头功,一气之下竟然发病而死。听说刘整死了,南宋权臣贾似道来了精神,他于1275年正月亲率南宋最后的精锐十三万人、二千五百艘战船逆江而上,迎击伯颜的大军,决定南宋生死存亡的一战到来了!2月,宋军抵达芜湖后,非但不积极部署御敌,反而先遣返元军战俘,原来贾似道想故技重施,向伯颜乞和,但遭拒绝。无奈之下,贾似道只得下令步军指挥使孙虎臣率7万兵马列阵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长江中),同时命水军统领夏贵率2500艘战船横亘江中,他自己率后军驻扎鲁港(今安徽芜湖南)。
“丁家洲之战”是宋元战争中的一场在1275年长江发生的主要水战,可以称得上是南宋与元朝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根据史书记载,在这场战役中,因为贾似道的逃跑,主力并未损失殆尽的南宋军队,节节溃败,引发了一系列的溃逃,就连临安知府洪起畏也跟着一起逃跑了。
可是千年之后,考古专家发现了临安知府洪起畏的陵墓,使得大众对这场决战有了新的认识。战役信息都来自于洪起畏的墓志铭。洪起畏夫妻合葬,被发现时已经被偷的差不多了。所幸墓志清晰完整,而且极具研究价值。
《宋史》中记载贾似道抽调了南宋精兵十三万迎战,途中贪生怕死逃跑了。因为贾似道的逃跑导致丁家洲战役的惨败。这个时候,贾似道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南宋臣民群起而攻之,贾似道也一直被贬,直到被发配充军。在充军的途中,贾似道被仇人所杀。
因为丁家洲之战是决定性的战争,这直接意味着南宋的灭亡,即使之后再怎样的抗争也无法弥补了,所以根据《宋史》里的描述,贾似道是直接导致南宋灭亡的人物。
而洪起畏的墓志中提到了这次战役,洪起畏说,贾似道在战败后,也一直很努力地收集溃兵,想要继续作战,然而无能为力。同时他还提到,当时贾似道并没有想逃跑,最先逃跑的是步军指挥使的前锋——孙虎臣,他一逃跑,后面的仗无法再打下去,然后,贾似道才跟着逃。
史料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说明有多个版本,而与墓志的记载有很大的出入。专家分析中认为,墓志是由当事人亲自撰写,可信度是高于史料的,当这两者之间有出入时,一般以墓志为准。
在这一战役的描述中,不管是洪起畏本人还是了解他的族人,都不可能在墓志中替贾似道进行辩解。而且不管是谁先逃跑导致的失败,当时的镇江都已经是空城无法改变,基于这样的原因,墓志内容的可信度又提高了很多。
丁家洲一战过去了千年,到底事实真相如何,我们无从得知,这背后的一切,就待后人再继续挖掘分析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1273年,坚守多年的襄阳被攻克,南宋军队抵抗蒙古入侵的防御中枢被切断。随着蒙元军队的高歌猛进,长江中游的大量宋朝地方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迫于恶劣的形式,一直希望回避与蒙古正面交战的南宋权相贾似道,不得不亲自出马。但在一场水陆同时展开的正面决战中,他与南宋最大规模的军队被北方强敌完败。
自南宋与蒙古的战争正式开打,临安的小朝廷就对自身的定位非常清晰。由于见识过蒙古军队在长江以北的纵横千里,宋军一直都对在陆战中击溃对手是不抱希望的。他们只能以过去抵抗金国军队的方法,用水军守护长江天险,用城防拱卫战略据点。
但蒙元帝国的特殊思维,也让宋朝方面在刚开始很不适应。在通过走西南方向,迂回攻灭金国最后的主力军部队后,蒙古人就爱上了这种大费周章的迂回战略。所以在攻打南宋的初始阶段,他们一直尝试通过拿下四川,占据长江流域的上游。这种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极有可能是在投靠蒙古的汉化幕僚推动下敲定的。
问题是蒙古霸权对于麾下军事资源的整合也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大汗死后的贵族会议,又会让前线指挥官回师草原。这就让蒙古人在初步攻入四川后,又匆忙后撤。作为回应,宋朝马上加强了在四川方面的整体防御。等到蒙古军队再次返回,战斗激烈程度就超过了以往。这种模式的轮回,在短短十多年内发生了数次。加上蒙古人为大汗之位而展开的各种内战,愣是让疲惫的南宋又坚持了许久。
今天的宋粉们,总是津津乐道南宋是抵抗蒙古帝国时长之最,却都忽略了分兵四川对南宋整体防御策略的影响。由于唯一依仗的防线,全部集中在长江沿线。所以宋朝有限的军队都沿着江岸,依次展开。加之多余兵力还要拱卫首都临安及附近地区,让小朝廷很快就面临了财政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双重压力。
蒙古人特有的草原发散性思维,又在关键时刻给了南宋以致命一击。日后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亲自领兵,经过吐蕃地界,攻入大理。随着大理的沦陷,大量的吐蕃与南蛮军队,加入蒙古一边。宋朝的整体防御,也因此后庭大开。若非忽必烈在之后的战争中,执意攻下襄樊两城。南宋可能以更快的方式,被蒙古击败。
到了大厦将倾的1273年,襄阳城倒在波斯人打造的回回砲之下,南宋方面也明白,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在第二年一系列中小规模战斗中,已经初步培养出一支水师兵力的蒙元,顺利的将整个长江中游占据。南宋残军被沿着长江,截成两断,典型的首尾不能相顾,陷入江局。
1275年,经过冬季休整期的蒙元军队,继续沿着长江东进。原本位置险要的安庆,在屡战屡败的大将范文虎率领下投降。长江以南的江西沿线也望风披靡。在临安城里训政的太后谢道清,强令权臣贾似道出战。
贾似道在南宋朝廷以周公自居,并且已经执掌朝政多年。在与蒙古帝国最初的冲突中,他的欺上瞒下便发挥了恶劣效果。起初,他提出割让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并像宋朝习惯的那样,缴纳岁币。在蒙古人终于同意这个建议后,他又因为已经对内宣布史诗大捷,而坚决不履行协议。虽然他在斗蟋蟀与玩弄政治方面,很有天赋,却最终不得不被自己的恶行,推上战场。
蒙元方面,曾经随旭烈兀西征中亚的大将伯颜被任命为灭宋主力军的统帅。这位信奉涅斯托利派基督教的蒙古勋贵,早就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见识了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军队。他的对手名单中不仅有声名狼藉的刺客组织阿萨辛,也包括了最后死在巴格达的最后一任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以及阿尤布王朝在叙利亚的驻军。他的盟军中不仅有善战的中亚具装武士,也包括来自亚美尼亚王国和安条克公国的十字军骑士。
伯颜此次率领的大军,总数号称10万人之多。但扣除各种杂役、民夫与水手后,真正的战兵不会超过50000。除了为数不多的蒙古骑兵外,也包括了少量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阿速骑兵。其他骑兵则来自蒙古一路征服过程中收纳的突厥、契丹、党项。女真,乃至北方汉军。这些北方的汉人部队,同样也构成了蒙元步兵与水军主力。尽管在装备与组织上,他们和对面的南宋军队并无巨大差别。但其本身大都是北方多年混战的幸存者,绝非没有见过战争的新兵蛋子。至于来自西亚的工匠,则继续为蒙元大军维护致命的配重抛石器--回回砲。
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战争经验的贾似道,则带着号称13万人的大军,驻守在扼守下游位置的丁家洲。他一面继续向伯颜求和,一面将一些俘虏的蒙古战俘遣返。当最后的努力也被拒绝后,这位斗蟋蟀高手才开始布置战阵。
宋军的核心其实是由2500艘大小战船组成的水师。这其中即包括了可以用于航海的黄鹄船,也有用于长江水战的楼船及各种艨艟小船。自知蒙元已经有不少水军的宋人,显然已经在水战上花费心思。为了让临时搜集起来的水师,能够以一个完整的整体进退,大中型船只全部被用铁链相连,小艇则在大船附近机动。这样,在未来发生的战斗中,宋军一方不仅有数量优势,还能在较为稳定的平台上应战。
此外,足足70000人的步兵被部署到长江两岸。由于担心水师前进后被敌人从后方包抄,贾似道制定了这个水陆相互掩护的战略。这也几乎是他手里可用的最后一点战兵了。
为了配合水师防御,宋军步兵摆出了他们钟爱的三叠阵。这种在少量重步兵附近放置拒马,保护大量弓弩手的静态防御战术,曾是宋军对抗辽金数百年的保留项目。在大凡能摆出此阵的战役中,宋军步兵往往能顶住强攻。反之,则可能发生万人大军被十几名敌军骑兵追杀的惨剧。
面对宋军摆下的大阵与进攻举动,伯颜一开始有所犹豫。虽然知道宋军战斗力不如自己麾下部队,但在复杂的长江两岸开打,他心里依然没底。何况在西方,摆出连环船战术的舰队,往往是用于进攻而非防御的。宋军摆出不多见的进攻态势,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时候,蒙元军队所特有的多族将领优势,发挥出来。水军中带头的不乏吕文焕这样的南宋降将,他们不仅熟悉长江的水文条件,也对宋军的虚实了如指掌。那些蒙古与色目将领也都是经历过大战的老手,有着宋军将领普遍缺乏的勇武之气。至于北方汉军万户们,也都知晓服从号令。伯颜就在这群幕僚的围绕下,制定了对贾似道的作战计划。
1275年4月16日的晚上,蒙元军队主动发起第一次攻击。10艘精心打造的木筏从上游顺流而下,直逼宋军水师的铁索连环船队。木筏上堆积了大量柴火,在点燃后照亮了整个江面的天空。
由于元军的这一活动,是在对手眼皮底下完成的。所以宋军显然对可能发生的火攻,早有防备。在很快用小船清除了火攻筏后,他们彻夜都高度戒备。位于全军后方坐镇的贾似道,却没有对部署做必要的调整。他期望继续以即将进攻的态势来组织对手。但他的部署,也让战斗不强的宋军分散在长江两岸。之后的几天里,整支舰队也需要时刻提防下一轮火攻的来临。
经过5天的折腾,南宋守军已经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显出疲态。处于兵力弱势的蒙元军队,则在21日主动发起攻击。这一举动显然出乎了贾似道的预料,也让很多执行命令的前线将领,不知所措。当元军的水师与两岸的步骑兵同时开进,疲惫不堪的宋军已经被浩大的场面所震撼。
整场战役,首先以蒙元军提前布置好的投石机打响。这些来自西方的致命攻城武器,在射程上超过了宋军手拉式抛石机。南宋的战船上虽然有投石机,但大都是单兵使用的最小型号。面对敌人炮兵阵地射来的石弹,毫无还手之力。大量的主力船只被铁索绑定,在得到命令前是不准松绑的。于是,当容易成为目标的大船被命中浸水后,与其绑在一起的数艘船只也几乎失去了机动力。船上水师,则在被动挨打中士气大跌。
之后的第二轮石弹,落入了两岸宋军的阵地。他们由于摆出静态防御的三叠阵,无法及时调整所谓位置。回回砲虽然射速较慢,却依然在心理上对守军有着巨大冲击。蒙元的骑兵也很快在三叠阵外围,与宋军骑兵交手。战斗力羸弱的后者,很快被蒙古人从亚洲各地搜罗的骑兵武士们击溃。位于内侧的南宋步兵,依然尝试用弓弩还击。但很快赶上来的蒙元宋军,也用一模一样的武器,向只能站着不动的守军射击。
伯颜的部将阿术,则带领一支由数千艘大小船组成的水军,杀向长江中央的宋军船队。后者在几天几夜的心里折磨中,损耗了大部分体力,又因回回砲的石弹而胆战心惊。当面对杀来的蒙元水军,根本无法组织像样的抵抗。敌军迅速接近,并登上了贾似道为他们准备的稳定平台,海战瞬间变成了陆战。被分割在各船上的南宋水军,遭到了元军小船的集中攻击。正如他们的陆军同僚,也在两岸被逐个击破一样。
面对这种水银泻地般的全面强攻,明白大势已去的一线将领们,首先开始逃跑。督战陆上战事的将领孙虎臣,在见到元军攻入三叠阵后,调头就跑。他的离开,也让原本在阵内据守的宋军,全面崩溃。以轻装远射武器为主的他们,一旦离开设防阵地就成了骑兵策马追杀的羔羊。不少人从小路奔走,才免于一死。
接着,已经失去对船队控制的夏贵坐小船逃跑。他的离开,让不少宋军砍断铁链,自信撤离。由于场面混乱,不少船拥挤在一起,被后续追来的元军水师拿下。杀红了眼的阿术,甚至亲自掌舵,撞击江面上的宋军小艇。然后挥舞帅旗,让乘坐小船的汉军,继续追杀。
在后方目睹这一切的贾似道,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鸣金收兵的同时,自己乘坐一艘小船,顺流逃往依然有重兵防御的扬州。13万南宋军士,则在他身后惨遭屠戮。伯颜的骑兵,甚至一口气追杀了150多里,彻底打散了宋军重新组织起来的希望。南宋与蒙元帝国的最大一次正面决战,就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结束。
丁家洲之战的灾难性结局,无疑宣告了南宋抵抗力量的覆灭。虽然在此后,依然有张世杰与文天祥这样的人,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但小朝廷所剩不多的精锐,已经大部分损失在长江两岸了。
躲入扬州的贾似道,在第二天开始陆续收拢残兵。但对他失望透顶的宋军,纷纷头也不回的继续逃跑。贾似道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而南宋王朝的结局也已经被他的努力所定格。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这成为宋元局势的转折点。
蒙古国的国号全称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汉人有时会称为“大朝”。忽必烈取《易经》里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元”为新国号。“元也者,大也。在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大之至也。”“大元”,不仅象征着忽必烈准备继承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大业,也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纳入中原王朝体系,名正言顺地侧身于夏、商、周、秦、汉、隋、唐大一统的王朝序列。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行为意味着对蒙古的背叛。但对于北地汉人来说,则可谓万众欢欣,因为从此他们不用再为给蒙古人卖命而感到羞耻,他们将效忠的是一个代表儒家传承与华夏正统的朝廷,至于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是哪一族的,没人关心。而对于很多南宋的士大夫与豪族来说,投降元朝,这是顺应天下改朝换代的大势,而不是降敌,这似乎完全对得起祖宗。
定“中统”年号,都燕京、立朝仪,以“省院台大臣御前奏闻”取代蒙古传统的忽里勒台会,直到改国号“大元”,忽必烈依据中原各个朝代的传续建立了一个起码在表面上完全汉化的朝代,这个新生的“大元国”也成为南宋投降一派的上佳遮羞布。至此,南宋大势已去。
1273年二月,在攻下襄樊后,对于下一步的出兵,忽必烈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以姚枢、阿术、阿里海牙为代表的主张立即挥师南下,直取临安。徒单公履曾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阿术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备见宋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而以许衡为代表的则主张暂缓发动全面攻宋之战,因为攻占襄樊用了五六年时间,军费开支占去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忽必烈的财政体系也有些不堪重负。
忽必烈最终还是采取中和意见。一方面扩军备战,刘整继续训练水军五万多,又在各地造船三千艘,同时签军十万。另一方面,在宋元前线组建军管机构,由伯颜进行总负责,并加强屯田投入,以缓和财政的压力。
忽必烈为发动灭宋之战,迅速地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与此同时,南宋方面的备战却是一片混乱与无序。
襄攀失陷后,朝廷对于主要责任人只是做了表面上的惩处:范文虎官降一级,到安庆府任知府;李庭芝及其部将苏刘仪却遭贬黜。因为吕文焕投降而提出辞呈的吕氏集团将官,全部继续留任。
同时,升汪立信为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负责对元军的全部防御战。高达为宁远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后来降元);夏贵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后来降元)。
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问罪”南宋,宣布南伐的开始。
忽必烈在诏书中,将罪过直指南宋唯一还能领兵统帅的贾似道,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皆彼宋自祸其民”。包括拘留郝经、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已峻功硕德而自比周公,欺人寡孤儿反不如石勒。
可谓字字诛心。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一份来自敌国的诏书,却成为后人视贾似道为“奸臣”的铁证。
1274年三月,贾似道因母亲去世开始丁忧。
1274年七月初八,宋度宗“违和”,一天后突然去世,享年35岁,而且是在还没来得及册太子的情况下就去世。去世后一个月,忽必烈发布了攻宋诏书。宋度宗的去世,有许多的疑点,然而史料缺失,后人只是关注于他的“夜御三十女”,却没办法认真审视这个传说中荒淫羸弱的皇帝到底对南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前线的元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临安却陷入皇帝去世,办国丧、立新帝的混乱之中。正在丁忧的贾似道,在执政、侍从、两省台谏的共同上疏之后,终于被起复,重回朝廷。
七月,元军兵分两路,左路由中书右丞博罗欢为帅入侵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右路集襄阳主力二十万,以左丞相伯颜为帅,沿汉水而下。九月攻占沙洋,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战死;十月底攻占复州(今沔阳),逼临鄂州;十二月,进围汉阳军,都统王达八千兵战死,夏贵向东逃回庐州,朱禩孙向西逃回江陵,权知汉阳军王仪投降;鄂州守将程鹏飞、张宴然投降,元军轻松地突破了长江防线。
在这期间,在襄阳投降的吕文焕发挥了极其得要的作用。在其出面招抚下,从1274年年底到次年的一个月时间里,沿江制置使、知黄州陈奕降敌;知蕲州管景模和副将吕师道(吕文焕之侄)降敌;知江州钱真孙和守将吕师夔(吕文焕之侄)降敌;知安庆府范文虎(吕文德之婿)降敌;池州张林降敌;五郡镇扶吕文福(吕文焕从弟)降敌。
吕文焕虽然未必是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却无疑是宋亡的最大推手。
1275年正月十五,贾似道上了一份出师表。“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向使先帝以及两宫,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为信,听臣之出,当不使如此。”这份出师表,道尽贾似道的沧桑与无奈。然而即使如此,太后太后谢氏,依然要求他坐镇临安,不想让他在外领兵。无奈之下,贾似道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三个孙子全部留在临安,作为人质,才得以离开。
正月十六,贾似道率十三万兵、战船二千五百艘,以孙虎臣为前锋,夏贵为水军统帅,屯驻于丁家洲(现安徽铜陵长江中)。二月十九日,宋元开战,元军在大江两岸架设回回炮,利用步骑夹江列阵。在火炮与战船的冲击下,三面受敌的南宋水军由于缺乏陆上军队的掩护,死伤惨重。先逃的是夏贵,这人能活到82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是孙虎臣,他总结了一点:“吾兵无一人用命也”。
元军顺势掩杀驻于鲁港(现安徽芜湖南)的贾似道中军。军心全失的十三万南宋主力,大部分被歼,军队完全崩溃,沿江州郡“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唐震城破自杀,通判万道降敌,知和州王喜降敌,建康都统翁福降敌;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可与、知隆兴府洪益皆弃城而逃;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从隆州逃至抚州;江淮招讨使汪立信自杀而死。
贾似道人生的最后一战,就此悲惨的结束。临安,已经赤裸裸地呈现在元军的面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元军攻占鄂州(今武汉武昌)后(参见鄂州之战),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步军10余万,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锋,沿长江东进。宋沿江诸将,多为吕氏旧部,及元军至,皆望风归降。至元十二年正月初,元军至黄州(今湖北黄冈),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降。
- 雍正帝之领导力:解码“阳”面帝王之术的现代启示
- 诸葛亮与刘备伐吴:历史迷雾中的战略抉择与权力平衡
- 李渊父亲四子争爵:非嫡非长何以承袭唐国公?
- 李文忠:从乱世孤儿到开国名将的传奇人生与家族浮沉
- 一代明君朱元璋的五大历史倒退之错:权力集权下的制度困局
- 历史上真实的殷开山:唐朝开国功臣的传奇人生
- 范增:项羽身边的谋士,其水平实力究竟几何?
- 文翁:公学始祖与治水名臣的双重传奇
- 魏文帝曹丕之死:历史迷雾下的真相探寻
- 李广利是草包吗?汉武帝为何仍重用他?
- 汪废后: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后,却被皇帝废掉
- 飞将军李广的长孙李陵,为何被武帝满门抄斩?
- 姜维北伐中原时费祎的反对态度与深层考量
- 明朝名将吴良:十年镇守江阴的传奇与结局
- 三国风云中的郝普:从蜀汉太守到东吴廷尉的悲剧人生
- 汉朝建立功臣排名解析:萧何居首与张良位列六十二的深层逻辑
- 曹魏与东吴结盟后:为何对手热衷活捉关羽,却对赵云“无人问津”?
- 魏文侯成功的秘密:礼贤、革新与战略的完美融合
- 赵昚的皇位之路:猫与处女的特殊考验
- 刘备失败后为何未归成都:非不敢,实不能
- 王旦轶事典故与后世评价:一代贤相的德行风范
- 薛奎:北宋名臣的治世风骨与后世评价
- 三国名将实力解构:张郃与赵云的军事对决与战力落差
-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为何未全盘接手元朝领土?
- 从市井到战场:关羽张飞骁勇善战的基因密码
- 王郎:乱世中的双面人生
- 李世民放过侄女却斩尽侄子:权力博弈下的理性抉择
- 关羽与张飞单挑:巅峰对决的胜负推演
- 义渠王之死:权力博弈下的温柔陷阱
- 蜀汉军队仅十万人,诸葛亮为何执意北伐?
- 康熙削藩与吴三桂造反:历史天平上的必然与偶然
- 朱高炽:体胖多病之躯,何以承继大明江山?
- 朱标:史上权力最盛的太子与朱棣的“不可能”之路
- 褚英之死:从战场骁将到权力祭品的悲剧人生
- 黄霸:西汉循吏典范的治世人生
- 忠义与知遇:纪信与韩信共赴明主的心理密码
- 鸿门宴后的权力棋局:项羽为何未处置项伯?
- 黄宗羲:明末思想巨擘的传奇人生与学术革命
- 庙号之争:朱允炆与朱厚熜追封父亲背后的权力密码
- 幽州猛虎的陨落:公孙瓒的崛起与败亡密码
- 威震塞外的白马将军:公孙瓒的崛起与陨落
- 黄宗羲:博学多才铸就的思想与学术丰碑
- 徐晃:三国武将中的中坚力量与排名之辨
- 范祖禹:北宋史学星空中璀璨的孤光
- 文彦博:北宋政坛的定海神针与翰墨大家
- 文彦博:翰墨遗风与典故流芳的北宋名相
- 打破荧幕滤镜:历史上的和珅究竟是何模样?
- 湖湘学脉的奠基者:张栻教育思想与理学体系的多维建构
- 鳌拜手握四十万大军,为何至死未动谋逆之心?
- 濂溪先生周敦颐:理学开山的人生轨迹与精神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