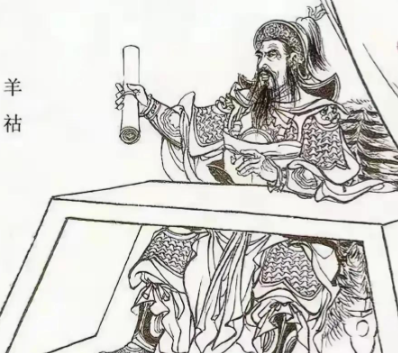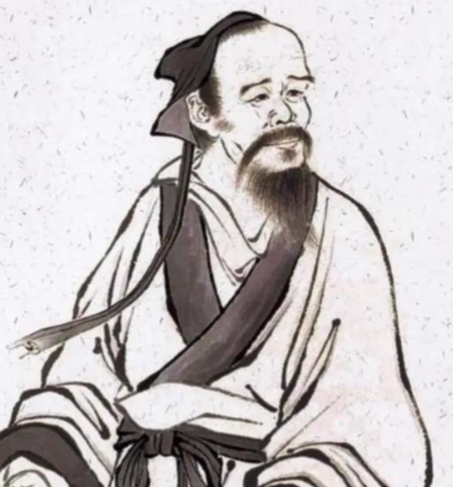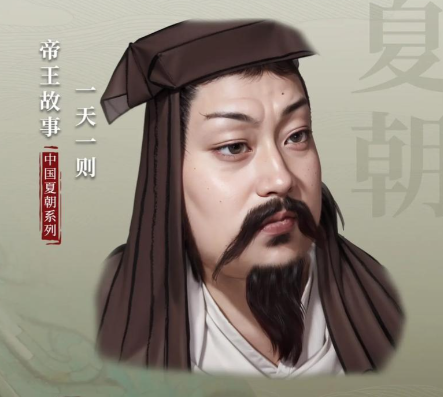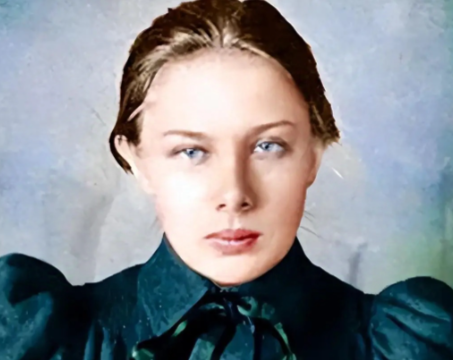在古典诗词的意象长河中,“何逊扬州”已成为咏梅、怀古与文人风骨的经典符号。杜甫笔下“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诗句,苏轼“空教何逊在扬州”的慨叹,以及李清照“寂寥恰似,何逊在扬州”的孤寂,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梅花、扬州与文人情怀的浪漫叙事。然而,这场文学盛宴的起点,却是一场因时空错位引发的历史误会。
一、历史真相:南朝扬州与隋唐扬州的时空错位
何逊(480—520年)是南朝梁代诗人,其生平与扬州的关联源于《梁书》与《南史》的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何逊任建安王萧伟的法曹参军,随其驻守扬州。此处的“扬州”实为南朝的治所建业(今南京),而非隋唐以后广陵(今扬州)的别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均以建业为扬州刺史府所在地,广陵则属南兖州管辖。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才将广陵改称扬州,此后的扬州才与今日的地理概念重合。
何逊的咏梅故事亦存在争议。据《南史》记载,何逊在扬州任法曹时,于官署后植梅一株,每逢花开必邀友人宴饮赋诗。后迁官洛阳,因思念梅花而请调回扬,抵扬时正值梅开,遂“彷徨终日”。然而,这一记载最早见于宋代苏轼《次韵王定国倅扬州》的注解,南朝文献如《梁书》《何逊集》均未提及此事。宋代学者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已指出:“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更明确考证:何逊诗中的“扬州”实为建业,后世误将南朝扬州与隋唐扬州混为一谈。
二、文学重构:从历史掌故到文化符号

尽管历史真相存疑,但“何逊扬州”的典故却在文学创作中完成了从事实到意象的蜕变。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杜甫的奠基:唐代诗人杜甫在《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中首次将何逊与扬州梅花关联,以“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表达对友人的思念。杜甫或许误读了何逊的生平,但这一诗句却为后世提供了将梅花、扬州与文人情怀相结合的经典范式。
苏轼的推波助澜:北宋苏轼在《次韵王定国倅扬州》中写道:“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其《忆黄州梅花五绝》亦云:“扬州何逊吟情苦,不枉清香与破愁。”苏轼不仅强化了何逊与扬州的绑定,更赋予其“吟情苦”的文人形象,使这一典故从历史叙事升华为精神象征。
南宋以降的普及:南宋以后,“何逊扬州”成为诗词中的常见意象。李清照《满庭芳》以“寂寥恰似,何逊在扬州”自喻孤寂;周紫芝《浣溪沙》借“趁他何逊在扬州”表达对梅花的期盼;陆游《欲离均阳而雨不止》则以“不如何逊在扬州”羡慕友人能赏梅赋诗。这一典故逐渐脱离历史语境,成为文人表达高洁品格、怀才不遇或时光流逝的通用符号。
三、文化影响:扬州与梅花的千年羁绊
“何逊扬州”的典故不仅重塑了文学传统,更深刻影响了扬州的文化地理。尽管南朝扬州实为南京,但隋唐以后的扬州仍主动承接了这一文化遗产:
地方志的平衡术:清代《江都县志》在“古迹”篇中详列“东阁”条目,既引述杜甫、苏轼等人的诗句,又援引杨慎、张邦基等学者的考辨,最终以“‘东阁’沿误已久,未便遂没其名,存之以备参考”的结论,既保留了文化记忆,又维护了历史真实。
梅花的文化象征: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李鱓、高翔等人均以画梅著称,其作品中的梅花或“临风傲雪”,或“铁骨冰心”,恰如何逊诗中“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的写照。黄慎《踏雪寻梅图》题款“独有梅花知我意,冷香犹可较江南”,更将梅花视为知音,延续了何逊以梅自喻的传统。
现代的文化传承:今日扬州的梅花书院、何园等景点,仍以“何逊咏梅”为文化标签,吸引游客探寻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尽管这一关联源于误会,但正如清代学者杭世骏所言:“前人为杜甫诗所作的注虽无中生有,然‘解舍梅花’之事,已教扬州人不免尴尬,亦教扬州名胜多出个东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